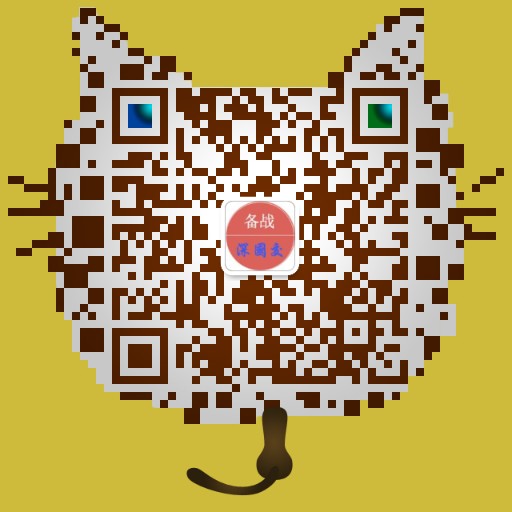当前位置:首页 » 深国交哲学社 » 正文
-
自接触社会学来有几年了。这几年常回想高中那个在学校走廊不顾一切向前奔走的自己,那时她内心对人文社科的热爱在盛大地燃烧,让现在的我既感到羡慕又感到怀念。那是十分珍贵的情绪燃料。那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茶余饭后交谈的日子,思考的激情在每一个散步的夏夜将尽之时无限缱绻的瞬间。而那时的我们也不完全是热烈无畏而明亮的,尤其是在疫情期间,面对社会的种种困境和问题,那些理想主义被现实的车轮一次次碾碎的瞬间现在回想起依然心生无奈。在十六七岁的年纪,面对现实与理论产生的撕裂是恐惧而绝望的,悲观而无助的,但更是痛苦而愤怒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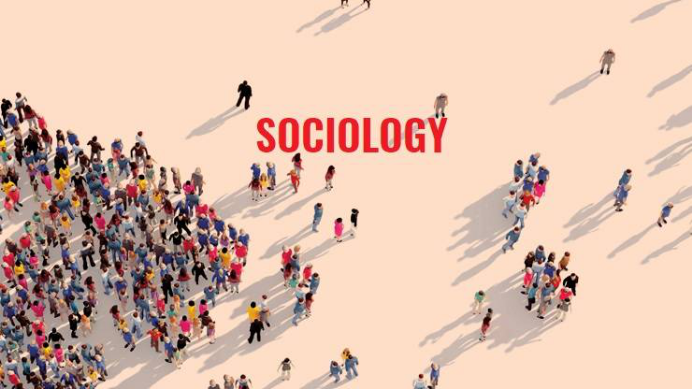
社会学的结构分析范式似乎过早地将一种巨大的分析框架放在我们面前,而通过这种分析框架去接触社会问题的我们无法避免地走向对结构最深处的批判,而又基于现实的条件限制,这种批判总回落到这个发问:So What?
So What? 这个问题我从高中问到现在,在大学阅读各种艰涩文本的时候,在面对抽象到无法与自身经验对话的理论时,在面对社会学的理论工具根本无法(can’t),也不能(shouldn’t) 解释个人困境时,在面对西方理论体系与中国社会的割裂时,在面对各种高深概念华丽词藻叠加不知所云的文本时--我总是会问这个问题。而至今,我和四年前的我一样,依旧困惑不安,没有任何答案,甚至产生了更多更多无解的问题。
原以为自己高中时对于复杂与模糊的灰色地带的接受程度已经被颠覆翻新过了一次,现在的我,在这四年时间里,越来越能与没有答案的问题周旋,与没有答案的问题产生的巨大的不确定性共处,这其中滋生的重重精神危机,价值重估,迷茫与不安,让我不仅仅对社会学这个学科的意义一次次产生怀疑,也是对自己的一次次发问: What kind of life I should live? What do I believe?
在大一这一年,我经历了人生中第一个existential crisis. 由于这两年来自己一直在一巨大的不确定性与流动之中怀疑拆解更新自己的想法,始终无法找到合适的时间与精准的语言来整理过去自己究竟有何新的收获。各种彼此冲突无法调和的张力,以及经历本身与语言的滞迟,重建一种新的自我秩序变得愈发困难。在这个时间点上,鉴于本人身心状况似乎趋向了一种新的“稳定”,终于可以通过一种回溯型建构的方式来自我分析一下过去两年学习社会学的心路历程。
我主要在问自己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What is the role of sociology? 社会学要回答的/提出的问题是什么?社会学是怎么尝试回答/重新发问的(theory paradigm, epistemology, methodology)?
第二个问题:What sociology can do? 社会学的政治实践意义/日常生活意义?说白了,社会学对我们普通人/社会上“有什么用”?(application, activism, political significance)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社会学对指导我日常生活的行为实践是否能提供一种价值规范,能否回答人的价值意义类/具体生活实践问题。
这都是挺大的问题,我不打算像写学术论文一样,我也并不是以回答问题的目的来写作的。I don’t know where I will end. “Answer the essay question!” -- 这次我不打算在心里总是提醒自己这点来写作。这些都是提问比答案有意思得多的问题,且都是(没有答案)有很多答案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我在生活的捶打中问出来的,没有读过专门的认识论方法文献,纯属个人对社会学以及个人生活经历的一些反思与总结,不代表学科任何观点,感兴趣的话鼓励大家多多读一些(啃不动看不懂)的文献(哈哈)。基于本人的生活与学术已经搅和得一团糟,已经无法分清是学科的问题,还是提出了一个自身的问题了。
我们知道每一个学科都有其局限,社会学对其自身无论是理论认识论还是方法保持极强的批判性,以及社会学者对自身的自反性,一直都是是社会学旺盛生命力的来源。由于我对社会学的热爱让社会学的边界愈发变得模糊,它给我一种无孔不入地渗透感,它内化于我的思考自我、社会、万物的一种思维方式,它是如此包容广阔的一种分析范式,以至于我一如既往强烈地爱着这门学科,也因此痛苦而困惑着,深感沉重与疲惫着。
身边朋友和家人总是担心我问我:“会不会因此总是感到痛苦呢?” 不痛苦是不可能的。我总是想着挑战去看看社会学这门学科的最大可能性是什么样的,把我的生活当成实验室,我把世界当成我的研究场域,在与各种institutions/agents不断地撕裂碰撞中,在这个过程中我总是大喊,太失望了!太糟糕了!太混乱了!太累了!太痛苦了!我无法承受!但是跌跌撞撞疯疯癫癫中我似乎也终于生产出一些属于自己的知识了(?)。
“在他们看来,知识始于我们认识到日常认知具有欺骗性,即我们所勾勒的现实图景并不是真正的现实,我们大多数人都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没有意识到我们信以为真、以为不证自明的大部分东西不过是在社会生活的暗示下产生的幻象。因此,知识始于击碎幻象,即幻灭。知识意味着穿透表象、追根溯源,看到赤裸裸的现实。“知道”不是占有真相,它意味着透过表面现象积极、批判地朝真相不断努力靠近。” -- 艾里希·弗洛姆 《占有还是存在》
以上这段话是我前段时间读自己很喜欢的一个精神分析学家看到的,当时读来尤为感动。这是我第一次在文本中看到用”幻灭“来形容求知过程的,这精准捕捉了我求知的感受。由于社会学的批判性质,学习社会学的过程对于我来说一直是一个解构的过程--一种近似于残忍的“幻灭”伴随着让人灵魂颤栗的觉醒,这两股力量总是彼此交织。其次,弗洛姆在此还指出了此解构过程的性质是一个“无限接近”的状态--“批判地朝真相不断努力靠近”。
我以前是认为社会学家是可以捕捉“真实”的(social reality), 在此我指的是一种经验式的真实,比如,一个社会现象,一群人的某种行为模式,社会中的某种改变。通过概念和理论,比如Habitus(Bourdieu),微妙的阶层差异在日常肢体,语言符号中的表达与再生产,我们得以看到社会分层背后的“真实”--是一种隐密的社会不平等再生产机制。
这种“揭穿”现象表层看到背后权力叙事,透过结构因素解构个人困境的分析,一开始给我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社会学经典的个人的就是社会的the personal is social/structural ,让我重新看到自己所在的社会阶层,性别困境,由此从一个结构和宏观的角度俯视自身从而重新理解了自身和社会的许多问题。
去从一个结构层面structural level来分析理解个人,这样一种从personal narrative转向结构的叙事能够重新识别(recognize) 日常琐碎的烦恼,从而一遍遍地安慰那些囿于个人困境的痛苦的人们--这永远都不是你的错。由于你意识到这个社会话语的规训永远站在权力那一边,由于你意识到这个制度本身在保护哪些人在忽视哪些人,由于你知道who wins and who loses, 由于你知道how power works, 由于你意识到institutions的错误能够被discourse掩盖,你就能意识到自己在这权力天平中的位置,以及重新定义自己的遭遇到底“是什么”。
我想我们能拥有的一个基本共识是,首先永远不去指责自己/受害者的问题。受害者有罪论是rape culture。为自己夺回解释权是那些处在永远向权力天平下端的人们能为自己赋予的唯一首要权力,然后再想办法调动资源、知识与技能去反抗和争夺。无论如何你自己对自己解释权和定义权要捍卫住,如果不死死捍卫那权力的机制必然轻易将其误读,稀释,冲刷,剥夺。This is how power and discipline works. It always works through self-blaming and self-doubt. 它如此隐秘有效,借你之手将你毁灭。
解构当然是必要的。解构给予人安慰,托住破碎的身体。即使它终究无法去抗衡权力结构,但是在个人的日常实践中,通过解构能够重新看透规训的逻辑,将被其环绕中的自我暂时拉扯出一段距离,虽无法完全解脱其束缚,但在一次次的识别与分析后,绝能够保护自己不让自己轻易内化甚至认同其逻辑来二次伤害自己或他人。不成为权力的帮凶,已需要艰苦卓绝的努力。
我也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拼命学习的理论和知识是多么重要,我需要更多这样的知识和理论,让我得以去重新理解这个世界一切的荒谬和复杂,从而牢牢地在自己要摔倒的时刻落实坚定有力地兜住自己。这是首先我能为我自己所做的的赋权。
借理论之眼去再看一遍那些经历和遭遇,去再看一遍,去重新看一遍,去看到那些隐藏的逻辑和叙事。
权力在日常生活中的全方位渗透,是全方位的,是无边界的,是不自觉的,在我们日常面临的对话中,在自我潜意识的规训中,在对后果的预测和行为的调整中,在害怕中,在日常的表演性中,在服饰与物质的解读中,在肢体的挪动和身体占据的空间中……甚至在我们无意识的领域中,镶嵌进我们的身体和欲望中,与权力的周旋是everyday struggle。
这两年学习社会学我觉得最大的感受是,不管是哪个理论家还是哪个分支,社会学提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 What is power, how power works. 我觉得这个是社会学要回答的核心问题,但如何将这种批判落实到日常实践中,是一个我时常发问且觉得更加复杂的问题。
有时我会社会学这种结构式的“升华” (elevation)渐渐感到疲惫。或许是当经验式的生活慢慢抽象成一种power structure(patriarchal classist racist capitalism) 的分析框架,我习惯性地让结构式分析先行去稀释真实的生活体验,这种经验与理论之间的紧张让我感到困惑。我意识到社会学的结构式分析已经深深地内化为我思考问题的一种方式,但是同时意识到这种思考方式的局限性与带来的无力感。
社会学是十分强调结构的。上大学前我还感觉个人与结构在社会学中的拉扯是50%vs50%吧,但是上了大学意识到社会学简直从头到尾流淌着structuralism的血液,如果要谈到个人主观能动性也感觉是戴着结构的脚镣蹩脚地跳跳舞。
最直觉的感受就是,尽管社会学家们费劲心思想去调和一下他们浓浓的structuralism论调,在这种巨大的结构框架前,社会学学生无可避免地都是悲观的结构主义论调。我身边的朋友们每次谈到什么主观能动性啦,个人的自由啦,什么meritocracy/neoliberlism啦,都有一种愤怒感。一听到什么individual blaming怪罪个人的言论就条件反射地暴跳如雷要骂人。记得在上microsociology的课上(讨论为数不多的注重micro-interaction而不是结构的社会学家的时候),教授让大家投票,“individual VS power”, 班里所有人都投power。
精神状态令人堪忧的社会学子们,每日每日在elite bashing和society blaming的“高谈阔论”中,在“战火纷飞”的校园中惶惶度日(奔走街头)。
导致的结果就是对自由意志主观能动性这类高度怀疑。毕竟咱们的社会话语近几年来一点都不缺“做自己”这样的言论,社会学家们扯破喉咙用尽全力去扳回这套话语大喊“individual choice is a submission to power structure!”(个人选择是屈服于结构的另一种形式)--然而社会学的这套话语使社会学学生深深信服,却无法让学术界外的人听到。留下一群破防的社会学学子们终日破防地看到个人和他人在结构划下的格子框框中终日兴奋地跳舞,而对那些跳得正欢的人,身为社会学学可不忍心就这样上前告诉ta们:“You know what? (actually)You fall into the trap of power structure!”
omg the world is collapsing , don't you feel it?
我们知道幻想、故事、欲望、宗教是必要的。我们无法不抛弃它。我们获取可以抛弃它,但是我们的身体不会抛弃它。眼泪、爱欲、失落,破碎后又依然为自己找到新的精神支点的惯性,这些循环往复的撕扯或许是最接近某种生命本质的事物。结构、逻辑、分析,思考,我们可以去借此接近真相,但是如果一开始这个真相就是让人失落的呢?如果这个所谓的真相本就是徒劳的呢?如果这个真相本就是无益于个体的生命的呢?
如果我们认定人无法拥有自由意志去与社会结构抗衡,这样强大的预设除了让我们去做推石头的西西弗斯,还是让我们为改变而付出某种微薄之力而燃烧生命呢?如果将个体纳入宏大的分析之中,看到的是冰冷如钢铁般所谓命运的东西,如果在人与人之间的争吵看到的是作为制度和结构的东西,将个人的抗争看作是无法超越社会分层的努力----我确实是感到某种程度上这种分析给予了我一个暂时的答案,但是伴随着这个答案带来的确定的解释和宽慰,也带来诸多复杂性和模糊性的死亡,甚至一种思考上的懒堕与行动上的踌躇不决。
我困惑着一个问题,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应不应该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用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去解释一种生命经验?为何要解释?我们要如何学会不去解释?是的,我看到个体经验诞生于种种社会因素的背景中,但是我依然不能仅以此去解释这段经验。我看到一个真实的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依然感到这些解释机制顿时被瓦解的瞬间,我要思考如何去解释对这个个体是有益且感到幸福的,不是吗?这一点儿也不是个关乎真相与机制的问题,不是吗?
比如说,我生病了,我病得很重,我去医院,我吃药,我抽血拍片,我在床上躺着。这个就是我生病的经历了。我的身体痛苦得很。脑子无法思考。我还要如何分析这段生病的体验呢?课堂上学的什么embodiement paradigm, narrative,疾病社会学的那些东西,如果我说和我的经历一点关系都没有呢?如果我的经历根本是无法被语言解释的呢?没有叙事、情节、只有断断续续的疼痛、挣扎、沉默与绝望,然后在片刻的安宁中为再次感知到身体的平静而庆幸珍惜?这个就是生病的人的经历了。如果你社会学家要为此做个研究整理出一套理论,也是可以的。于是我课堂上又学了一个叫anti-narrative的东西。
有的时候我发现世界在知识的洗礼下变得如此清晰、赤裸、残暴。一切都可以被解释,溯源、构建、整理、归纳。语言与文字的力量可以覆盖万物的边角。没有细节再被放过,没有问题不再不被提出。流动的不确定性也变得清晰,谎言的不真实性也变得真实,暗流涌动的挣扎也浮出表面,一切在我看来,一切,都是清晰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调动某种视角去重塑它、与它对话,一切痛苦皆能找到某个支点去安抚与理解。然后,连虚无的感受也变得异常清晰,清晰而真实,如失眠的夜晚一样稀松平常。
在这样的清晰之中,我与世界的距离变得坚固,我的底色逐渐如磐石般稳固牢靠,但我却感到惘然若失。我看到我曾体内曾升起的感受在被逐渐稀释然后慢慢流失,我感到世界不再像一个球体,如今我穿过它,只能直直地走到底,捕捉到单一的信号,然后放在那里。我用重复的语言去描述与归纳,我用过去探索得到的某种规律去支持我的生活,我用我身体的记忆在与人交往与对话。我感到一种被抽空的平静。
我看着我的生活,看走在路上的人的生活,我发现每个人都在这世界这个球体的不同支点上构建自己的生活。如果生命一开始各自降临的支点就根本不一样,那差异与比较的概念或许自一开始就不存在。
如果世界如球体一般无限丰富,那任何人在这个球体的创造就都是可能被许可的。
如果一开始降临在这个支点的资源与条件就不一样,那就根本无法乞求人与人之间能拥有完全一样的生活,或者是让人去拥有相同的想法与目标。
如果生命本来就如此随机、仅有一次,草图,那人的生命一开始就是无法被经验化的,也就根本没有用语言解释,甚至被比较描述评价的必要性。
一切回归扁平的混沌之中。
我发现我的生活似乎充满了一种根本性的张力,一种绝对地成为自己与世界之间的张力,我预感到或许根本就没有人能完全地成为自己,其代价很有可能是被世界完全的抛弃进而走进疯狂亦或是我安全无法捕捉和预料的东西。我感到害怕。
如果确实唯一有资格描述和评价个体生命的唯有个体自己,而个体在很多时候却无法解释我自己,也无法做出最好的选择,那生命这个东西就是去承担责任,去向一切说“是”,然后继续,然后承担,然后......然后承担主体的命运吗?
如果说她已经在智识上完全看透甚至能预测自己生命的走向,但是她依然要走进生活的洪流,她的生命融入这河流中,然后她逐渐忘记,放下,再融入这河流中。如果我真要用语言去表述的话,依然显得太简单贫瘠了吧。但是如果生命她就是如此这般呢?
我感觉我又回到了哲学。每次我的思考都要回到这个领域,从大一学哲学开始,似乎一开始我就不认为社会学能回答这些问题吗?
我想,如果社会学的基本价值能够给予人的生活一定的指导与走向,我认为这一实践本身就是政治性的,是一种道德实践,是个体的主动选择,是在为自己的生命主动赋予一种要求或者原则,并相信其某种更宏观的意义(并不认为是一种更高的意义)。
女性主义,平等,这些价值或许能保护个体但或许也能带来更多的纠结与痛苦,但无论如何,个体总中感到宽慰、充满意义,更加相信生命本身,或许我想就是有益的。我目前是这么想的。我认为现在说理论知识能拯救一个人是不负责的,因为它也能让人走向死亡。思想是双刃剑,全看个人如何将其利用,我宁愿相信人在选择自己的思想和信仰上是拥有完全的自由意志的,或者说,正是因为这些思想和理论人才能够选择相信自己拥有自由意志去选择自己相信的生命。
但我现在更加希望,没有这些指导或许也是好的,不去思考这些或许也是更好的,不需要用理论和知识保护自己的世界才是好的。
只为爱,阳光与秋天的到来与烤面包的味道而感到幸福而充满希望,这样如教徒一般每日虔诚祈祷着的生活或许就是一切的开始与结局吧。
作者:Maggie推荐阅读:
版权声明:“备战深国交网”除发布相关深国交原创文章内容外,致力于分享国际生优秀学习干货文章。如涉及版权问题,敬请原作者原谅,并联系微信547840900(备战深国交)进行处理。另外,备考深国交,了解深国交及计划参与深国交项目合作均可添加QQ/微信:547840900(加好友时请标明身份否则极有可能加不上),转载请保留出处和链接!
非常欢迎品牌的推广以及战略合作,请将您的合作方案发邮件至v@scieok.cn本文链接:http://shenguojiao.scieok.cn/post/4828.html
-
<< 上一篇 下一篇 >>
社会学的边界
31639 人参与 2024年12月06日 22:40 分类 : 深国交哲学社 评论
search zhannei
深国交2024年英美本科录取小计
-

未标注”原创“的文章均转载自于网络上公开信息,原创不易,转载请标明出处
深国交备考 |
如何备考深国交 |
深国交考试 |
深国交培训机构 |
备战深国交 |
联系方式
Copyright www.ScieOk.cn Some Rights Reserved.网站备案号:京ICP备19023092号-1商务合作
友情链接:X-Rights.org |中国校园反性骚扰组织 | 留学百词斩 | 南非好望角芦荟胶 | 云南教师招聘考试网 | 备战韦尔斯利网| 备战Wellesl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