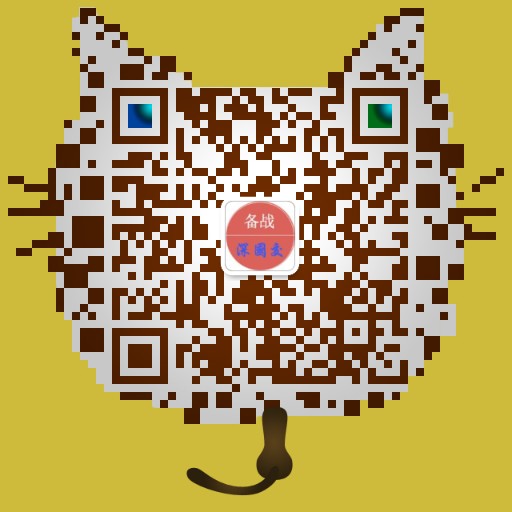当前位置:首页 » 深国交哲学社 » 正文
-
原载自(美)亚瑟·丹图(Arthur Danto)著:《叙述与认识》(Narration and Knowledge)的第一章,周建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1-20页。感谢西方史学理论读书坊公众号的图片与引言!
关于作者:
 翻译 / 周建漳
翻译 / 周建漳排版 / y² 在本章中,丹图区分了两种历史哲学:实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的历史哲学。不过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丹图将笔墨主要侧重于讨论实质的历史哲学的性质上。在丹图看来,与纯然是哲学的分析的历史哲学不同,实质的历史哲学是一种错误且含混的构建。一方面,它并非是哲学,因为其内在拥有与历史学相似的解说模式;同时,由于其非法地将历史学家组织过去的方式投射到未来中,导致它也很难实现自身史学叙述的目标。基于比对后丹图发现,我们关于过去的彻底把握总是预设了对未来的完全描述。因而,除非我们拥有一种合法的历史哲学,不然我们将不可能自洽的拥有完整的历史描述,而这份艰巨工作显然只有分析的历史哲学才能完成。 此外,依据丹图本人的说法,该书最关键的一章是第八章「叙述句」(narrative sentences)。在那里丹图详细地分析了历史写作中最基本的叙述形态,并阐发了叙事结构渗透于我们关于事件的意识中的观点。 注:本文的观点是深刻、引人思考、值得阅读的,并且推进了学科发展,但并不代表哲学社完全同意其观点。  实质的与分析的历史哲学
实质的与分析的历史哲学「历史哲学」一词涵盖两种不同的探索,我把它们称作实质的与分析的历史哲学。前者与通常的历史研究相关,也就是说,实质的历史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一样关注对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的记述,尽管他们所关心的不止于此。另一方面,分析的历史哲学则不仅仅与哲学有关:它就是哲学,只不过是运用于特定概念性问题的哲学,这些问题是在史学实践和实质的历史哲学中产生的。实质的历史哲学与哲学的关联并不多于史学本身与哲学的关联。本书所从事的是分析的历史哲学的研究。
我首先要分析的是除了记述过去之外,实质的历史哲学还试图做什么。有人会说,与即便最具雄心的通常史学著述不同,大致说来,历史哲学试图给出关于历史整体的描述。然而,这一说法一开始就会碰到一些困难。假定我们将现有历史著述的各个部分都放到一起,在此之上再加上其他的部分,它们足以将各部分间的所有空白填补起来,这样,我们最终就有了对所有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的彻底描述。这时也许可以说我们已经得出关于整个历史的说明,从而有了一种历史哲学。而事实上我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我们至多只是得出了关于整个过去的描述。因此,我们必须区分全部历史与整个过去,做到这一点的一个办法如下。
关于史学的典型看法是,史学家们感兴趣的是在大量细节基础上对特定的过去事件进行研究和撰述。在此,我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使用「事件」一词,但法国大革命显然是这类事件的一个例子,史学家们对之有兴趣加以研究和撰述。必定存在着大量这样的事件,对它们的发生我们只有极少的证据,还有大量的其他事件,我们认为它们一定发生过,除此之外,我们对之所知无几。简而言之,在我们关于过去的描述中有许多空白之处。然而,假定这些空白都被填满,从而我们对于所有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知道得和法国大革命一样多。让我们假设我们了解曾发生过的每一件事情;我们对于作为整体的过去有一个理想的编年,这仍然够不上我所说的实质的历史哲学所关注的历史整体,这样一个关于整个过去的完全描述至多不过是为关于历史整体的实质的历史哲学提供素材。素材概念是与理论概念相关联的,关于实质的历史哲学的简单看法是它意在发现与历史整体的观念有关的某种理论(所谓历史整体在此是一个有待澄清的概念)。我将根据这一看法界定两种不同的这样的理论,即描述性的和解释性的。
在此框架下,描述性理论探寻构成整个过去的那些事件的模式,并将之投射到未来,从而声称这些事件在未来要么是重现存在于过去事件中的模式,要么就是完成它。解释性理论试图对这一模式作因果式的说明。我坚持认为,解释性理论只有在与描述理论相联系的情况下才成其为一种历史哲学。存在着各种依照一般性概念——如种族、气候或经济因素——说明历史事件的因果性理论,但这些理论至多不过是对社会科学的贡献而不是历史哲学本身。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历史哲学,它表现为上述两种理论:描述的和解释的。从描述理论的角度看,它所给出的是某种阶级冲突的模式,任何阶级都在自身的存在条件中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并被它所推翻:「全部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历史的发展是辩证的。只要特定的因果性力量还在起作用,这一模式就会继续下去。按照不同的经济条件揭示这些因果力量就构成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性学说。马克思预言,由于与这一模式的持续相关的经济因素将变得不起作用,这种模式将在未来某一时刻终止。对于此后将会怎样,除了某些谨慎的乌托邦式的暗示,马克思显得不那么有把握。但他认为,那时「历史」这个词将不再有用。按照他对历史的理解,当阶级冲突消失,历史将走向终结,正如当社会中阶级不复存在阶级冲突就不存在了。而他,马克思所给出的只是关于历史的理论。在所有情况下,十分明白的是,「全部历史」涵盖比「全部过去」更宽的内容。它同时还涵盖全部未来,或者说,如果做出这样一个限定是重要的,涵盖整个历史的未来。下面我还会回到这个问题。
依照我所假设的方式看待史学与历史哲学的关系,我们可能被诱使将它理解为与观测天文学与理论天文学之间的关系相似的关系。据此,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在一个很长时间内所做出的包括关于已知行星位置在内的达到前所未有准确性的系列天体观测是值得称赞的,然而,他本人并未发现这些不同位置间可推广的模式(projectable pattern)。是开普勒(Kepler)成功做到了这一点,他经过艰苦努力发现,行星的位置可以在以太阳为焦点的椭圆轨道中被确定。这就好像我所说过的描述性理论,它有待牛顿去解释这一特定模式为何成立,也就是说,有待他提出一个解释性理论。历史哲学家有时按与我们所看到的相似的方式看待自己的任务。例如,康德这样写道:
无论关于意志自由可以形成什么样的形上理论,表现人类意志的行为就像所有其他外部事件一样,总是被普遍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按照关于规则的自然原理的观点,可以期望,当人类意志自由的活动被放在普遍历史的大尺度上加以审视,我们在它的运动中可以看到合规则的进程,以这种方式,在个体情况下看上去杂乱无章的东西,在整个物种的历史中却可以识别出人类原始禀赋虽然缓慢但持续推进的发展。……因此,我们得看看是否能成功找出一条这样一个历史的线索;而留待大自然本身去产生一位能据此撰写这部历史的人。大自然的确产生了一个开普勒,他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将行星运行的偏心轨道归诸于确定的规律;大自然又曾产生了一个牛顿,他以一条普遍的自然原因解释了这些规律。 假如不嫌过誉继续我们的比较的话,实质的历史哲学和一般史学的关系正像理论科学与科学观测的关系。以往有过并且现在仍然可能有一些学科没有超越单纯的观察,标本的收集,诸如此类。通常意义上的史学也许就是这样的一门学科。实质的历史哲学可能构成将史学带到科学认识的后两个阶段(分别是开普勒和牛顿式的层次)的台阶。实际上,「历史哲学」应该是关于历史的理论科学,它被当作「哲学」只不过是这个词过去老的用法的残存,如同物理学曾被称为「自然哲学」一样。开普勒所发现的规律虽说是建立在第谷所收集的资料的基础上的,但却超越了它们。它使天文学家不仅能将第谷所观测到的行星的位置被整合进一个融贯的模式,而且可以预测它们的未来方位,甚至那些开普勒时代未知的行星的方位。牛顿定律不仅仅解释了第谷和开普勒所知的事实,而且(在理想意义上)可以解释大量他们还不知道的事实。同样,人们迫切希望,一个超出历史学家所收集的资料水平的真正成功的历史理论不但能够将材料归结为一个模式,而且能够预见和解释未来的历史事件。可以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实质的历史哲学与历史的总体有关:所有过去与整个未来:时问的全体。与此相反,史学家只关心过去,只有当将来成为过去他们才关心它。因为,现有资料均出自现在和过去:我们现在不能收集将来的资料:而历史正是从事资料收集的工作。

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 1546-1601),丹麦天文学家、占星学家与炼金术士,著名的天文学家开普勒曾是他的助手。第谷在他的著作《彗星论》中提出了一种介于地心说与日心说之间的理论。他认为地球是一个静止的中心,太阳围绕地球作圆周运动,而除地球之外的其他行星围绕太阳作圆周运动。
这样一种描述对于实质的历史哲学来说过于慷慨,但它对于历史本身则过于吝啬。即便假设以往的历史哲学是某种成为类似于科学理论的东西的尝试,根据我们对它们的了解,我们也只能得出它们是相当粗糙的结论。的确,它们是如此的粗糙,将之与哪怕是开普勒那样简单的描述性理论相比较,现有的历史哲学理论也是无可言喻地不够格,几乎毫无预测力。解释的历史哲学,即使是那些最有影响的学说也好不过理论的提纲,而理论本身则尚待形成,更不用说经受了检验。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普通的历史描述(甚至不必是那些最杰出的),它们在自身的学科门类(genre)中看上去已经是高度发展了的实例,能满足可被运用于自身领域的学术标准,与历史哲学可悲地不能满足科学理论的标准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
更有甚者,历史描述看上去满足其标准的领域表面看来并不包含像连续许多夜晚报道行星位置的簿册系列这样的东西。很难将例如吉本(Gibbon)《罗马帝国的衰亡》这样的作品与布拉赫的观察笔记或任何一套科学观察的报道归为一类。或者不如说,历史自身中存在着类似某种活动的事情,在我们正在考虑的描述中,历史作为整体被拿来和它比较。在我的心目中,当历史学家运用特定技术鉴定文献与器物或确定事件的时间,或者确定罗利(Walter Raleigh)究竟是不是无神论者或确定某人的身份,他们所从事的就是这样的活动。这样的行动的确可以被实用地当作观察性的,产生出单义语句且很可能是真实的,例如「罗利不是无神论者」。但这根本不是历史研究活动之所在。在历史研究中也有将已知事实整合进融贯一致的模式这样的事情,对事实的这一组织在某种方面和科学理论非常相似,正如历史哲学与科学理论间的共同性。当然,它们并不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认可对未来的投射。不过,它们却的确具有某些预测力。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上关于过去发生事情的特定描述让我们能预见到关于过去所发生事情的一些进一步的事实,这些事实迄今为止不为我们所知:独立的探究将证实这一预见。被预见的事情发生在过去这一点不应该让我们看不到这样的事实,即这是一个预测,并且,如果你愿意,这是一个作为历史学家的我们在探索中随即会发现什么的预测,这与我们进行某项特定观测时预言我们在天空中将会看到什么的预言非常相似。因而,在南斯拉夫的不同地方发现三座具有考究的罗马风格的陵墓,了解罗马人将死者埋在路边的习俗,这预示着这些坟墓是坐落在一些主要的道路边,此后的调查可能证实这一预言。观察与理论的区别在史学中至少有一个相似者。史学描述与科学理论间也许有巨大的不同,但这一差别不会比历史哲学和科学理论间的区别更大。
进而,以为历史著述除了为历史哲学提供进一步的素材之外并不包含别的内容的想法是不恰当的曲解(第谷想要发现契合于他的观测的描述理论,但假定历史学家以这样的方式看待他们自己的「观察」肯定是错误的)。这并不是说历史学家所做的事情不能被以这样的方式看待,而只是说他们对自己的工作不作如是观。正像艺术家们不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为艺术史家提供素材,尽管事实上艺术家所做的事恰好是艺术史家的素材。在不同的上下文中,不论我们如何刻划历史的工作,眼前关于它的描述与实践中的史学家们关于史学目的及判断史学成就的标准的看法并不一致。接受这样的描述将在我们的作为一种理智性学科的史学观念方面引发一场革命。如果我正巧读到关于三十年战争的记述,它激发了我关于历史解释的思考,我们可以说写它的历史学家引发了某些哲学反思。但是,激发哲学反思并不是他记述这场战争的目的。我们所面对的就是这样的情况。一个历史学家竭力确立某一过去的事实,尔后,其他历史学家在描述过去的某一片断时使用了这一事实。在他同事的眼中这也许是也许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记述,但如果它不能令人满意,可以给出另一个描述。这一描述是与它所替代的描述同类的东西,但它正好满足同样的标准,对于这样的标准其他人注定是不满意的。这样的描述(对于历史描述必须满足的标准我得多说两句)多少是完成了的,对它们的任何改进仍然是史学范围内的东西。换言之,这样的一些描述并不是其他不同种类事情的预备,而是满足同样标准的同类描述的前期工作。
这样,史学与历史哲学的区别不在于后者给出建立在具体事实性发现基础上的解说而前者不是这样,史学和历史哲学都提供这样的解说。所以,如果历史哲学家所给出的解说要居于历史领域之外,它得是与历史解说大不相同的,做某些与史学所做的不同的事情。而且,如果它要在任何一点上像科学理论的话,我们当然会期望它是非常不同类型的解说,因为科学理论明摆着属于不同类别,与通常标准的历史解说遵循不同的标准。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历史哲学与标准的科学理论几乎毫不相同。如果说历史哲学和什么相似的话,那就是与标准的史学解说相同,除了它们给出关于未来的言说之外,而史学通常对此不加论说。
史学与历史哲学的相同并非仅仅基于这一事实,即历史哲学和史学描述一样往往呈现出叙述的结构,同时还在于这样的事实,在典型意义上,历史哲学倾向于给出关于所发生的事件序列的阐释,这与我们在历史中看到的十分相像,而与通常在科学中见到的情形很不一样。历史哲学使用的阐释概念在我看来在科学中是明显地不恰当的,这就是「意义」概念。也就是说,历史哲学致力于揭示依这个词特定地和历史地恰当的意思而言这个或那个事件的「意义」。洛维特(Löwith)教授提出以下的观点作为对实质的历史哲学的一般刻画。他说,它是「关于普遍历史的系统阐释,这一阐释与历史事件及其序列借以被统一并指向一种终极意义的原则相一致」。
我们该如何理解「意义」这个词的特殊用法,它与通常我们使用这个词时所说的例如一个词或一个句子或一个表达的意义大不相同?简略地说,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我们通过参照一个更大的时间性结构而将事件认作是有「意义」的,这些事件乃是这一结构的组成部分。意义的这一用法并非是完全陌生的,例如,想一下当我们说一部小说或戏剧的特定片断没有意义,它「缺乏意义」(lacks significance)时所触及的要点。在这里,我们想说的是它没能推进后续行动,它是肤浅的,从而在美学上是不恰当的。但这当然是只有当我们整部小说成竹在胸或整部戏已经完成时才能做出的对某一特定片断的判断。在此之前,我们只能说对某一片断的意义还不知道,尽管我们预想它在整个情节发展中有其地位和作用。事后,我们会说它有这个或那个意义(除非它没有引起任何东西,它完全没有意义,这对于一个好的戏来说是一个瑕疵)。我强调,只有在回溯中和着眼整个作品时我们才有权说某个局部具有某种特定的意义。可是,当我们头一次置身作品之中时,对于整部作品我们恰恰胸无成竹:此时,如果有什么东西在我们看来触目地没有意义,我们得等着瞧到底是否真的如此;假如有什么东西在我们看来有某种特定的意义,同样,我们得等着瞧自己是不是对。根据后来的发展,我们常常得修正此前关于某一局部意义的看法。这种意思的意义(sense of meaning)也适用于历史中。现在法国大革命已经过去,我们可以说网球场誓约(Tennis Court Oath)的意义是什么——即便是事件的参与者对此也可能有错得离谱的看法。依照这样的理解,我们可以将历史哲学看作这样的尝试,它在历史整体的语境中看各种事件的意义。历史的整体与艺术的整体是相似的,但这里所说的整体是历史的整体,它包括既往过去、当下现在以及将来。和一卷在握从而能以某种权威说这一事件或那一事件的意义不同,历史哲学家面前并没有历史的整体。他面前所有的至多是一个片断——全部过去。但他根据历史整体进行思考,仅仅根据他已经掌握的片断推求历史整体的结构应该是怎么样的。同时尝试按照他所构想的整体结构说出这一片断的各部分的意义。

网球场誓约(Tennis Court Oath),是一份由576名法国三级会议第三等级代表和少数第一等级代表于1789年6月20日签署的誓言,该誓言要求所有签署者在法兰西王国的宪法制订和通过前绝不解散,以向人们表明政治权利属于人民及其代表而非君主。这一事件通常也被认为是法国大革命诞生的标志。 我很同意洛维特教授的主张,看待历史整体的这一方式在本质上是神学式的,或者说无论如何它与神学对历史的解读有结构上的相似性,后者在历史中微言大义式地看出神圣的计划。我认为,看到这一点是富有教益的: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然而,他们却倾向于透过本质上神学的观点看历史,仿佛他们能感知到神圣的计划,只不过这计划不是哪个神的。无论如何,如果我对它们的描述是正确的,实质的历史哲学显然关注于我所说的预言(prophecy)。预言不单是关于未来的陈述,因为,预测(prediction)就是对未来的陈述。预言是关于未来的一种特别种类的陈述,我要说,暂时不做进一步的分析,它是关于未来的历史性的陈述。预言家是以只适合言说过去的方式言说未来的人,或者说他是以将未来当作既成事实的方式谈论现在。预言家以通常只对未来历史学家才可能的视角对待现在,对于后者,现在事件是过去,其意义是可辨识的。
就在这里我要重提先前关于实质历史哲学与史学相关联的主张。举个例说,现在我们看到历史哲学是如何与普通的历史描述相类似的。而且我们能理解为何有时历史哲学甚至被归到错误的类别中,仅仅被当作普通史学著述在宏大尺度上一个特别富于雄心的例子:「马克思、斯宾格勒、汤因比们的宏编巨制的问题几乎不可能是因为它们是史学,而在于它们的宏大。」相似性在于这样的事实,历史哲学非法使用了「意义」的概念,而它在通常史学著作中有着合法的使用。稍后我会讨论由与意义概念的联系引起的=些问题,但眼下只要指出在历史探讨中通常所说的意义是如何被归之于事件的就够了。例如,我们知道某B所完成的事情在相当程度上应归于A的工作对他的影响。在历史中要知道A的工作的意义就是期待这样的回答:其意义在于对B的工作的影响。显然,这一含意的「意义」并未穷尽意义(significance)概念的全部意思:一本诗集也许是有意义的,仅因为它内在地是伟大的诗。也许可以这样说,除非我们在一些非历史的其他意义上使用「有意义的」一词,我们将无法在历史的意义上使用它。也就是说,事情可能是这样,我们发现B的工作是内在地有意义的伟大成就;因为如此,我们在B的传记中可能将他第一次见到A的著作这个插曲看作充满意义的,的确是承载着命运的。当然了,B的同时代的人对这一相遇的意义一无所知,因为B的伟大作品当时还没有产生。他不拥有我们所有的东西,即那些只在与A的著作相遇后才可能有的信息。在此之后,传记作者可能把这一插曲抽取出来当作B一生中具有最重要意义的事件。同时代的人不可能这样看待它:他也许认为这不值一提。同时,A的工作的惟一价值或许就在于它对B的工作的影响。
让我们在这一联系中思考一下某些很常见的情感类型,它们与我们对自己的行为与过失的记忆及评价相关联,例如,后悔或自责。典型地,通常我们这样表达后悔,「如果我事先知道……」我们在此所抱怨的通常是对未来的无知,这一无知被时间消除,因此,我们现在知道自己行为或无所作为的后果,这是我们过去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一般说来,我们的意思是,假如我们当时知道我们现在知道的东西,我们就不会那样做了。这样的说法当然是费解的。例如,如果我知道E将发生,那么,「E将发生」是真的,这样,E必定发生。如果E一定发生,那么,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它的发生,或者令「E将发生」成假。因此,后悔是无理的。一方面,如果我能采取行动阻止某事的发生,那么,它就不是必定要发生的。并且,如果我真的阻止了E,「E将发生」就是假的,从而我不能说知道E将发生。如果我对将来可以做某些事,那未来就不可知;如果未来可知,则我们对之就无所作用。对于这个出自亚里士多德的古老悖论,我们以后得加以考虑。但眼下可以指出的是,「如果我已经知道……」是不可坐实的:如果我已经知道了,我也就做不了什么了。而后悔的先决条件是,我们在行动时没有看出自己的行动具有我们事后赋予它的意义,这一意义我们是在与之相联系的未来事件的启明下知道的。但这是关于事件的历史建构的一般洞见:历史事件被不断地重新阐述,它们的意义在我们后来具有的信息的基础上被重新评价。由于他们拥有这些信息,历史学家可以说出历史的同时代人和见证者无权说的东西。
在历史的层面上,追问某一事件的意义就是追问只能在某一故事的整个上下文中才能回答的问题。同样一个事件依其所处的故事,换言之,依与之相关的不同组后来事件而可以有不同的意义。故事构成了事件在其中获得意义的天然语境,与隶属于一个故事有关的标准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目前我还无法涉及。所谓标准,即通过诉诸它我们可以说,就某一故事而言,事件E是它的一部分而E'则不属于它。不过,显而易见的是,讲一个故事就是将某些发生的事排除在外;就是不言而喻地援引标准。同样明显的是,我们只能讲这样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如果我们知道与事件E相关的未来事件,则E作为相关事件出现在其中。因此,在某种确切的意义上,我们只能说关于过去的真(true)故事。正是这一意义有时被实质的历史哲学所冒犯。运用与历史学家所使用的完全一样的意义概念,即意义预设了事件被安置在故事中,历史哲学家试图在后来事件发生之前寻求特定事件的意义,而恰恰是在与后来事件的联系中,这一事件方获得其意义。他们投射在未来的模式是一个叙述性结构。简言之,他们试图在故事本身可以被正确地讲述之前讲述故事。而他们所感兴趣的当然是整体的故事,即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故事。这当然不是说每一事件都将会是故事的一部分(故事之为故事必定要将一些东西排除在外),而是意味着,在其他事情中,历史哲学家将寻找有意义的事件,那些属于整个历史故事的事件。因而,历史哲学家组织历史的模式就是历史学家所使用的模式。但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区别不仅在于特定的宏观性。它同时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与某种关于未来的主张有关。
发现未来将发生的事情有很多方式,甚至有很多给出未来事件的历史性描述的方式。做到这一点的一个确定的方式是等着看所发生的事情,并写出关于它的历史。但历史哲学家缺乏耐心,他想要在现在就做循规蹈矩的历史学家尔后才能做到的事情。他想在未来的视野下(实际上就是终极的未来,因为,必须有一个所有故事的结局)看现在和过去。他企图能以某种方式描述历史,这种方式在事件本身发生的时间段中通常是办不到的。有一些我们在史学著作中常常碰到的叙述,在本书中我将主要关注它们。它们具有历史话语的模式特征——是充分合理和被视为真的描述,但在恰当的时态转换下,我们会发现,如果它们是在所描述的事件发生的时段中被言说,就几乎是无理的和不可信的。一个历史学家可能会这样写道:「《拉摩的侄儿》的作者生于1715年。」可是,试想假如有个人在1715年的那个时刻这样说「《拉摩的侄儿》的作者刚刚诞生」,那将会是多么奇怪的一件事情。如果有人在1700年用将来时态说这件事情,那就更令人困惑了。对任何一个人来说,这样的一种说法在1715年意味着什么,更不用说在1700年了?当然,也许有人,例如基于狄德罗家族中的男性历代都是文人这一点预见到狄德罗会生为一个作者,甚至是百科全书派(「一个百科全书派在你身上诞生了」)。但当涉及潜在作者的一本尚未写出的著作的标题时,这就超出预测了:它牵涉到以一种先知的腔调说话,即依尚未发生的事情来说现在(「你作为救主而降生」)。而实质的历史哲学所欲提供的正是这样的一种描述,它完全是参照后来发生的事情即在时间上处于所描述事件的将来的事件给出阐述。事实上,他们所做的是在发生之前写所发生事情的历史,并且,基于关于未来的解说给出对过去的叙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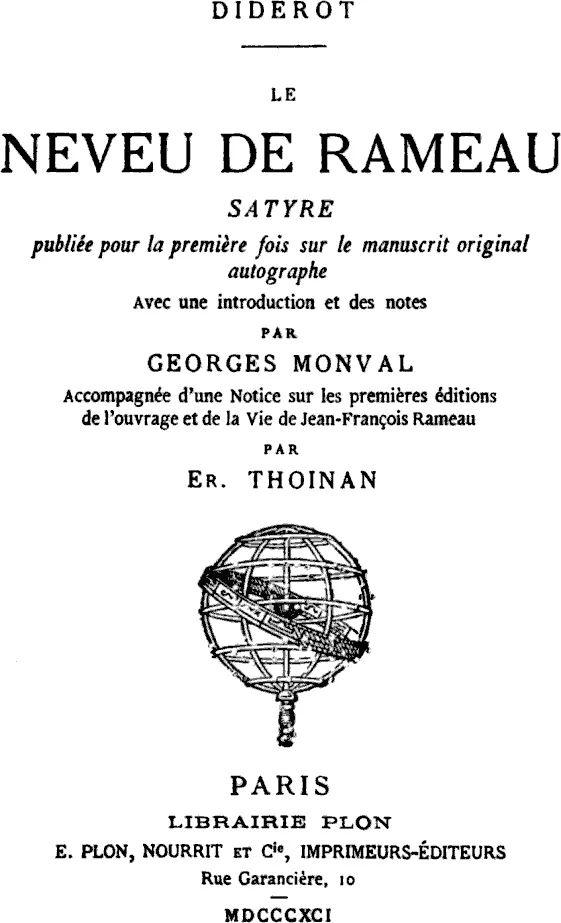
《拉摩的侄儿》(Le Neveu de Rameau),是法国思想家狄德罗(Denis Diderot)创作的虚构哲学对话集。这部作品写于1761-1762年,但并未在狄德罗生前发表,后由歌德首先于1805年翻译出版了德文版。作品主要由作为哲学家的「我」(Moi)与著名音乐家拉摩的侄儿(Lui)的对话构成,其中侄儿是主人公,他是一个道德堕落者,古怪而充满矛盾,是崇高和卑微,理智和非理性的混合体,而「我」则在故事中充当了一个说教的角色。狄德罗借助侄儿的生活经历表达了一种辩证的道德观,并辛辣的讽刺了启蒙时期部分思想家的观念。
在我看来,关于实质历史哲学的这一方面在哲学上既有趣又奇怪。评论家有时在历史的意义和历史中的意义之间(meaning of history and meaning in history)做出重要的区分,以此质疑整个哲学式历史的合法性。对某一事件意义的要求意味着接受某种上下文,事件在此中被认作是有意义的。这里说的就是「历史中的意义」,对这样的意义的追问是合法的。通常,事件在其中成为有意义的那个上下文是一个有限的事件集,后者共同构成一个事件在其中是一个部分的整体。因此,彼特拉克之登上冯杜山(Petrarch’s ascent of Mt Ventoux)在一组事件中是有意义的,这组事件共同构成文艺复兴(并且在这一背景中也许并不具有独特的意义)。但我们可能同样追问文艺复兴本身的意义,而这随之又要求更大范围的特定上下文,等等。有较宽和较窄的上下文,而历史作为整体显然是所可能有的最大的上下文,寻问历史整体的意义就是得出这样一个上下文框架,在其中对意义的追求是合理的。由于不存在一个比整个历史更宽广的上下文,历史可以置身其中,这对实质的历史哲学是一个重要的批评,但在我看来,这对它并不构成本质上的危害。哲学家也许会说,整个历史是从某个完全非历史的上下文如神圣意志中获得其意义,进而说上帝不管怎么说都是在历史和时间之外的。其次,他也许会像我已经表明的那样指出,历史意义的确定依赖于某些其他的、非历史意义的确定,例如,因为我们把B的工作在某些相当不同的意义上看作(也许)是有意义的,A由于其对B的影响而具有历史意义。哲学家接着可能会说,我们不可能言说作为整体的历史的意义,但历史意义绝不是意义的惟一类型。最后,他可能会强调,「作为整体的历史」并不必然意味着所有那些已然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也许并非任何事情都构成历史整体的一个部分,整个历史也并非是所可能的最为广阔的上下文。我们已经说过,故事必定将某些事情排除在外。例如,对于黑格尔而言,发生在西伯利亚的事情就不被看作是历史的组成部分。他并不否认在西伯利亚发生了各种事情,只是认为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在历史事件的宏观进程中并不具有任何意义,而他所关心的恰恰是关于后者的故事。在对历史整体意义的讨论中,他将之设定为:向着绝对精神的自我意识的运动。历史中所发生的任何事情是否有意义,均依其与这一故事的关联而得到确认。但是,黑格尔从来没有问过,绝对精神最终的自我认识(self-awareness)的意义是什么。或者说,如果他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他无疑就会转向一个与运用于通常的历史事件相当不同的「意义」概念。无论说历史哲学家所犯的错误是什么,我认为,它都不仅仅是对意义的两种意思的混淆。并且,我一贯认为,即使是一般的历史学家们也不可能只以一种方式使用「有意义的」这种说法。假如没有什么是具有非历史的趣味的,说某些事物(像是18世纪的那不勒斯绘画)仅仅具有历史的趣味是没有意义的。

彼特拉克之登上冯杜山(Petrarch’s ascent of Mt Ventoux),这是一件富有象征意义的典故,指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诗人彼得拉克曾在一封写给友人的信中讲述的自己攀登位于普罗旺斯的冯杜山的经历。这座山海拔1912米,彼得拉克声称自己是第一个为了看风景而攀爬这座山的人。虽然这一事件的真实性历来颇受质疑,但它的象征含义却超越了事实真假本身,通常被用以隐喻一种自我意识觉醒的「人文精神」,其内在蕴含着勇于发现自我价值的尝试和积极探索自然的努力。 我仍然认为实质的历史哲学是被错误地构想的活动,并且是建立在一个基本错误的基础上。我要说,它是错误的,因为它假定我们能在事件本身发生之前书写事件的历史。这一错误也许可以这样表达:这是这样的一种错误,哲学家试图对事件给出从时间上说是不恰当的描述,他们试图以一种这样的方式来描述事件,对事件的这种描述当时实际上是没法做到的。在此,我诉诸的是人们熟悉的事实,即我们是在那些事件发生之后才书写事件的历史。当然,这种诉求并不构成论证,哲学上恰当的问题是,如果这一事实成立的话,它为什么成立。科学家给出关于未来的看法,就像实际生活中我们所做的一样。但是,历史哲学家们所做的,或他们的职业要求他们做的那种关于未来的看法在我看来是可疑的。我坚持认为,他们关于过去和现在的主张与其关于未来的看法在逻辑上是相互关联的,因此,如果后者是非法的,那前者亦不能令人信服。历史学家对某些过去事件的描述参照那些在其之后发生的事件,对于所描述的事件来说,这些事件属于未来,但对历史学家来说,这些事件则属于过去,而历史哲学家则参照对于特定历史和历史学家本身来说均处于未来的事件对某些事件进行描述。我坚持认为,我们不可能享有令这样的行为成立的认识支点。我应该指出,对于历史来说具有本质重要性的事件组织模式不允许向未来的投射,在这一意义上,这些事件组织据以被产生出来的结构不同于科学理论。这部分地是由于历史意义与非历史的意义相联系,而后者则因人类兴趣的不同而各异。历史学家所讲述的故事不仅与其所处的时间点有关,并且与他们作为人所具有的非历史的兴趣有关。如果我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历史描述中存在着不可消除的人为及任意的因素,这使得像实质的历史哲学家所欲讲述的关于整个历史的故事,或就此而言关于任何一组事件的故事如果不说是不可能的也是极其困难的。历史哲学是智力的怪物,就像布克哈特(Jacob Burkhardt)曾经称之为的「半人半马的怪物」,尽管历史哲学很像史学且乐于作出只有科学才能给出的论断,但它既非史学亦非科学。
布克哈特写道,历史是第一级的学科(co-ordinates),哲学是次一级的(subordinates)的,而「历史哲学」这样的说法在语辞上是矛盾的。在一般层面上这一观点是正确的,但它对于史学作为处于第一层次的学科在什么方面与科学不同并没有告诉我们些什么,我们直觉地感到两者是不同的。这将我们引向分析的历史哲学,其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对这种类型的同阶关系(this mode of co-ordination)加以澄清。为此,必须记住的主要事实是,处于同一层级的事件在时间上是相互分开的,尽管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它们均属于过去,但是,它们本身分别处于过去和将来。它们两者是否以及为何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必须是过去,这是本书将要处理的一个主要问题。因此,如果说我们在此还能够谈论知识的话,在对我们关于过去的认识进行探讨时,我不能不对我们关于未来的认识的探讨感兴趣,因此,我至少应该在某种方式上像关注史学本身一样关注实质的历史哲学。我将坚持认为,我们关于过去的认识受到我们对未来的无知的重要限制。确定各种界限是哲学的一般任务,对这一限制的确定则是我所理解的分析的历史哲学的特定工作。/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Philosophia 哲学社
推荐阅读:
版权声明:“备战深国交网”除发布相关深国交原创文章内容外,致力于分享国际生优秀学习干货文章。如涉及版权问题,敬请原作者原谅,并联系微信547840900(备战深国交)进行处理。另外,备考深国交,了解深国交及计划参与深国交项目合作均可添加QQ/微信:547840900(加好友时请标明身份否则极有可能加不上),转载请保留出处和链接!
非常欢迎品牌的推广以及战略合作,请将您的合作方案发邮件至v@scieok.cn本文链接:http://shenguojiao.scieok.cn/post/2034.html
-
- 晚期阿尔都塞: 相遇的唯物主义,抑或虚无的哲学?/ 翻译
- 人口贩卖:历史延续与全球难题 | 一份书单
- 什么是战争中的正义:正义战争理论 (下)
- 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不快婚姻 —— 走向更进步的联合体 / 翻译
实质的与分析的历史哲学,分别是什么? /翻译
22884 人参与 2021年05月24日 11:36 分类 : 深国交哲学社 评论
search zhannei
深国交2024年英美本科录取小计
-

未标注”原创“的文章均转载自于网络上公开信息,原创不易,转载请标明出处
深国交备考 |
如何备考深国交 |
深国交考试 |
深国交培训机构 |
备战深国交 |
联系方式
Copyright www.ScieOk.cn Some Rights Reserved.网站备案号:京ICP备19023092号-1商务合作
友情链接:X-Rights.org |中国校园反性骚扰组织 | 留学百词斩 | 南非好望角芦荟胶 | 云南教师招聘考试网 | 备战韦尔斯利网| 备战Wellesl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