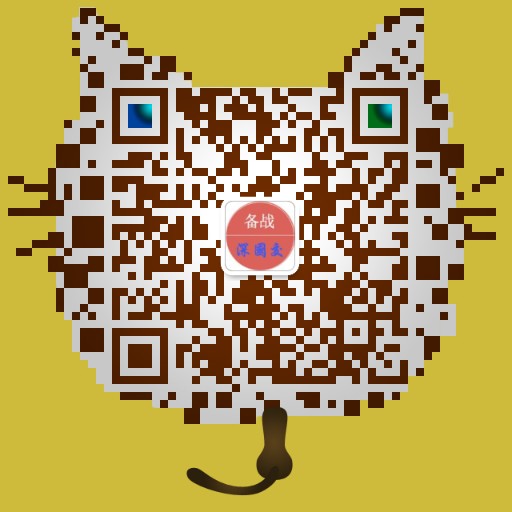当前位置:首页 » 深国交哲学社 » 正文
-
本文是1995年Julie A. Nelson创作的一篇具有简介性和开创性的期刊论文;其中的许多论点可以在她同年出版的《Feminism, Objectivity and Economics》一书中也再次得到了重申和扩展。作者论述道,虽然许多人认为经济学科是中立、公正、纯粹理性的,但其中却包含了男权社会的价值和偏见。在本文中,她分析了经济学模型、主题、方法论和教学方法四个方面中的男性偏见;本次的推送是这篇文章的下半部分。 作者不断强调的是,她所做的工作并不是创立一种和「男性经济学」对立的女性经济学。相反,这种对于男性偏见的考察和纠正能够使得现有的经济学得到改进,并且使得更多从业者意识到一些之前被边缘化的议题的重要性。因此,作者认为,来自女性主义的批评不是毁坏性的,而恰恰正是建设性的。来源:1995. "Feminism and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9 (2): 131-148.
关于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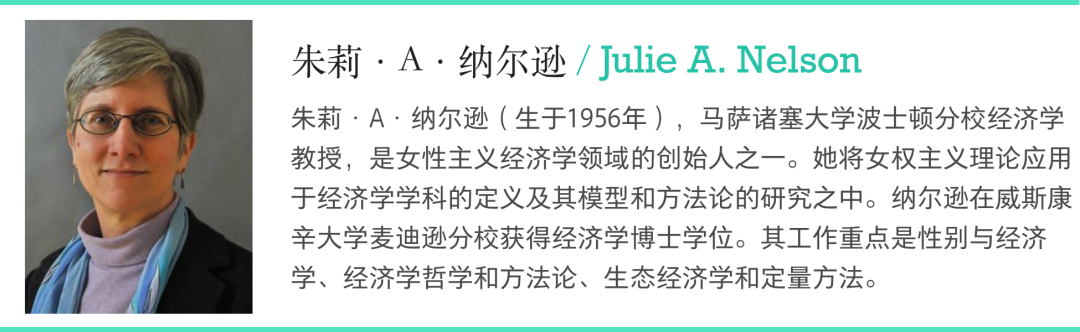
翻译 / bananafish 校对 / 星原,晖洁 排版 / fei 

经济学的四个方面 
(略,请见上一篇) 
经济学方法 虽然个人理性选择的模型可以用纯语言的方式表达分析,但在经济学学科中,普遍认为方法的质量主要与数学的严谨性相一致。严格遵守逻辑和数学的规则,假设和模型的形式化,计量经济学技术应用的复杂性——这些都是许多人心目中把经济学与社会学或政治学等「软」领域区分开来的因素。使用正式的和数学的方法(特别是以约束最大化的形式)也常常被假定可以确保经济结果的客观性。抽象和高度形式化的分析往往比具体和详细的经验工作更有价值,因为其证明的逻辑纯洁性和其与语境无关的普遍性。虽然优秀的写作和语言分析并非完全没有回报,但它们通常被认是真正分析的辅助。
女性主义学者认为,这种对知识和理性的狭隘观点是现代科学发展早期关于男性气质的遗留,尤其体现在笛卡尔哲学的主导地位(Bordo, 1987;Easlea, 1980)。注重于刚性和抽离非但不能保护经济学不受偏见的影响,反而束缚了我们的分析方法。的确,强调严谨、逻辑、科学和精确在防止分析是薄弱的、不合逻辑的、不科学的和模糊的是很有价值的。但如果这些是我们在实践中唯一珍视的美德,我们很容易成为其他恶习的牺牲品。
如前所述,强调男式的刚硬度而不强调灵活性会导致僵化。强调逻辑而不注意把握整体,会催生在无意义的推论中进行空洞的、脱离实际的练习。不关注人类价值的科学进步可以为非人的目的服务。那些为了精确而放弃了所有丰富性的论点最终变得非常单薄。

illustrated by Kotryna Zukauskaite 女权主义经济学家并不是唯一对经济学中对知识寻求的狭隘限制表示不满的经济学家群体,这种限制已经导致经济学家在更丰富、更实质性的分析技能方面缺乏教育和实践。虽然女权主义理论家为笛卡尔观点的心理和社会韧性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解释(并将其与模型、主题和教育学等领域的失败联系起来),但女权主义经济学家几乎不需要从头开始设想一个更充分的方法论工具箱。例如,唐纳德•麦克洛斯基(Donald McCloskey)写了大量文章,探讨提高修辞标准的可能性。McCloskey(1993)认为以隐喻和故事为基础的女性相关论证必须与以事实和逻辑为基础的男性相关论证享有同等的科学威望。作为一个实际问题,他甚至出版了一个关于改进写作的简短指南(McCloskey, 1987)。
美国经济协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的经济学研究生教育委员会(COGEE)最近表达了对过度强调脱离情境分析的担忧。它指出,经济学「研究生项目可能造就了一代有太多精通建模技术但对实际经济问题一无所知的白痴专家」(Krueger等,1991,第1044-45页)。虽然该报告将问题设定为(数学、技术)方法与实质之间的不平衡,但方法论本身没有受到挑战——这样的论点似乎表明,关于「事实、机构信息、数据、现实问题,应用和政策问题」(第1046页)的精华可以直接进行吸收。然而,只有通过掌握相应的技能,如搜索资料的方法和批判性阅读的技巧,才能仔细和系统地寻找关于真实经济问题的信息和良好的非正式推理。如果这些技能被认为有效并可以传授,就像是形式的和抽象的技巧那样,那么这个问题确实包括了方法的平衡问题。作为一个实际问题,COGEE报告包括了一些关于先决条件、课程大纲、课程内容、作业等具体建议,这些建议将使研究生院在某种程度上朝着教育增强学生分析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的方向发展。

图源:nytimes 对托马斯•迈耶(Thomas Mayer, 1993年)和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 1991年)等著名经济学家实证工作的具体细节的更多关注,也是对改变经济学价值体系的呼吁,女权主义者可以加入并支持这一改革。经济学家往往精通数学和统计理论。然而,在科学实证工作的其他方面,如寻找新的数据来源、改进数据收集、负责任的数据清理和质量评估、复制、敏感性测试、适当区分统计和实质性意义,以及数据归档方面我们通常表现出的技能要少得多。(例如,Dewald, Thursby, and Anderson, 1986)。经验主义工作的特点是对抽象理论的不断改进,且伴随着对具体细节的严重忽视,这被Mayer(1993,第132页)描述为「开着一辆奔驰沿着牛道开下去。」虽然近年来,一些期刊和资助机构试图通过要求敏感性测试和数据存档来提高专业标准,但期刊编辑、资助机构和论文顾问可以做出更多往这方面努力的鼓励。研究生研究委员会可以提供更多课程工作和经验,以便学习到好的技术。女权主义批判认为,减少使用抽离的「沉思」技术(Bergmann, 1987a)并增加使用「与自己的数据亲密交谈」技术(Strober, 1987)可能会更好。 对「硬」数据和「软」数据的价值判断也值得重新审视。经济学家对「询问人们行为的动机」持强烈的怀疑态度,以至于艾伦•布林德(1991)在最近一篇关于价格粘性的文章中花了整整一节来证明使用这种访谈调查数据的合理性。以笛卡尔的「证据」标准来判断,这样的证据可能是不可接受的。但从一个更广泛、更实用的学习经济运行的标准来看,这些数据可以被视为潜在的重要信息。例如,在国际女权主义经济学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Feminist Economics)最近的一次会议上,一名历史学家和一名社会学家就口述历史研究的技术进行了介绍。在这一领域克服偏见的经济学家可能会对那些接受过这种「软」和定性方法培训的人所表现出的技术的复杂性和对有效性和可重复性问题的重视感到惊讶。 在我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收集数据的过程中,个人经验也不应该被忽视。有些女权主义经济学家讽刺到,例如,在试图说服一个男同事的存在性别歧视时,通常不是丢给他10000个「客观」性别歧视研究,而是建议他观察一下自己女儿的日常。 那些相信科研的客观性只能通过研究人员和研究对象的冷漠和抽离,或者需要通过个人严格遵守特定的研究方法才能达到的人,肯定会痛恨这种允许让个人的、「主观的」立场和观点影响其科研结果的观点。而这种客观性的概念在女权主义分析中(以及在许多当代科学哲学中)被认为是笛卡儿错觉的又一个产物。事实上,追求客观性有一部分也应该考察一个人从个人经验中所获得的理念如何影响其研究。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 1995)将人们意识到个人立场的客观性称为「强客观性」,相对于在「弱客观性」中将视角的问题隐藏起来。阿马蒂亚·森(1992, p. 1) 同样认为,客观性始于「从立场出发的知识」。从主观观点到(强烈的)客观观点的转变不是彻底分离研究者与研究对象,而是把研究者与一个更大的批判社区联系起来。根据女权主义哲学家海伦·朗基诺(1990,第79页),「个人的客观性……在于他们参与集体的交换意见的批判性讨论,而不是在观察中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某种特殊的关系(比如分离,冷静)」。虽然关注结果的可靠性仍然是最重要的,但指导研究的标准是科研社区内部的,而不是外部的。形式化不是反映客观性的高度,而是被简单地看作一种工具。用克努特·威克塞尔的话来说(引用于乔治斯库-勒根,1971年,第341页),逻辑和抽象的作用是「促进论证,澄清结果,从而防止推理中可能出现的错误——仅此而已。」  经济主题
经济主题一篇典型经济学论文使用一个经济模型,经济方法,并且关于一个经济主题。前面已经讨论过有益于前两个领域的扩张,而关于主题的考虑也是至关重要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可能会认同经济学核心主题的广义定义是市场。经济学通常被定义为研究商品、服务、金融资产等物品交换过程的学科。根据这个定义,大多数妇女的传统活动——照顾家庭、孩子、生病和年老的亲属等等——被认为是「非经济的」,因此不适合作为经济研究的对象。事实上,家庭似乎经常从经济学家的世界中完全消失。经济学通常被定义为研究商品、服务、金融资产等物品交换过程的学科。根据这个定义,大多数传统上妇女的非市场活动——照顾家庭、孩子、病人和年老的亲属等等——被认为是「非经济的」,因此不适合作为经济研究的对象。事实上,家庭似乎经常从经济学家的世界中完全消失。当然,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来自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和其他所谓的「新家庭经济学家」(new home economists),以及博弈论在家庭应用方面的最新发展。这些作品的存在对女权主义者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他们确实把一些关于家庭问题的讨论带入了主流期刊。然而,他们严格遵循前面讨论的方法论和模型的狭窄标准,而且可能只有通过这些标准,他们才能保持他们在「经济学」上的认证。此外,让女权主义者感到烦恼的是,这部作品假设或认可关于性别的传统刻板印象。正如芭芭拉·伯格曼(Barbara Bergmann, 1987b,第132-33页)所说,贝克尔确实发展了家庭互动的模型,「解释、正当化、甚至美化了性别角色分化……说『新家庭经济学家』并不主张女权,就像说孟加拉虎不是素食主义者一样,都是重事轻说。」 
图源:the new yorker 尽管关于贝克尔的模型以及是否有可能使用个人主义理性选择模型来达成女性主义的目标一直存在一些争论,但这些争论发生在经济学的边缘。许多经济学家期望女权主义者会或应该集中精力与贝克尔辩论,这可能是一种避免回应女权主义的批评的便捷方式。这样,他们就将女权主义理论局限在一个和自己保持一定距离的安全区。 对于贝克尔来说,家庭之所以是「经济的」,是因为它可以通过选择和市场而被建模。但传统意义上来讲,家庭作为「经济」这种概念对妇女而言更加直观。从历史上看(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如此),许多女性的经济保障通常取决于是否「嫁得好」,而非自身收入。此外,在经济学家和人口普查还在纠结无偿家务是属于劳动还是消遣的时候,正在洗水槽的那个女性很少会有这样的疑问。 「什么在市场上流通而不在家庭中」的区分在经济分析中导致越来越多奇怪的死胡同和分歧。为何由市场(有时是政府)提供的儿童保育、老人照料和病人照料应该让经济学家来研究,而如果在私人家庭中进行就不值得经济学家研究了呢?与其使用市场化作为界定经济学的标准——或使用如上所述的理性选择模型——不如使用更广泛的经济学定义,比如,「供应」,来描述一个经济学主题,而不是使用充满性别歧视的假设去区分哪些不重要,哪些更重要(Nelson, 1993b)。 例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将经济学定义为不仅仅是选择和交换,还包括所有「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生产和分配,强调人类生存和繁荣所需要的东西。这些东西可能包括有意义的工作等活动,以及食物和医保等商品和服务。虽然某些商品和服务可能由在市场上活动的成年人自由选择,但许多商品和服务是由他们的父母在童年时期或其他家庭成员提供给个人的。它们也可以作为礼物或通过社区或政府计划提供。许多「必需品和便利品」的分配也受到传统和胁迫的强烈影响。 这种关于「供应」领域的经济学定义打破了「经济」(主要面向市场)活动和政策与家庭\社会活动和政策的区别。国民收入和产品账户中家庭生产条目的缺失说明了这种分歧是如何构建经济分析的,而许多女权主义者对这种忽视的关注是相对广为人知的(例如,Waring, 1988)。然而,女权主义者对是否应当优先将家庭活动纳入国内生产总值(gdp)存在一些争议。一些人认为越来越强调家务劳动只会美化家庭主妇的角色,还有许多人担心,由于目前认为儿童保育等活动的价值较低,评估出的货币价值也会偏低(Folbre, 1994b)。对GDP数字本身的重视程度也可能引发质疑。女权主义者可能会与其他人一起批评这种经常使用这种衡量市场和政府经济活动的粗糙标准作为经济福利标准的方法论上的还原主义。多层面的措施,其中可能包括分配和可持续性措施,以及诸如教育成就和健康等与人类相关的措施(Nussbaum和Sen, 1993年),将成为经济分析和国家决策和评估更充分的基础。例如,在关于发展经济、转型期经济和正在进行结构调整的经济的女权主义研究中,对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和商品的核算特别重要(Sen, 1985年;Bakkar,1994)。 比起对GDP的批评,很多人并不知道女权主义者在「如何在儿童身上投资、以及谁来承担这些成本」等问题上给予足够的关注(Folbre, 1994a)。例如,改善儿童营养或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的项目通常被认为是「社会」项目,仅仅是在财政项目的锦上添花,而不是旨在促进人力资本投资的经济项目。提高有偿托儿服务质量的项目通常被认为是父母的消费品,而不是对孩子和父母参与社区生活的必要基础设施的投资(特别是考虑到家庭内工作分配的性别刻板印象时,母亲扮演的角色)。标准的经济学分析和教育学倾向于强化这种琐碎的小事:回想一下,神奇的经济「蘑菇人」在他年轻时并不需要别人提供任何供给;同样,历史上女性提供这种直接供给的工作并不被视为「经济」。 
图源:Bostonglobe 作为一个具体的例子,考虑一下标准劳动经济学教科书中对人力资本这一主题的处理。它不是从关注营养、社会化、家庭和公立学校儿童的非正式和正式教育开始的,而是从年轻人选择大学的决定开始的(Ehrenberg和Smith, 1994)。当然,设计教科书时使用和学生直接利益相关的例子是有一些教学上的好处的,但似乎没有教学上的理由如此狭隘地关注高等教育。当我教授这门课程时,我发现添加有关早期人力资本发展的阅读材料,并要求学生从小时候开始反思他们的能力和抱负是如何形成的,对教学很有帮助。 主题的问题不能与先前提出的关于模型和方法的问题分开。不妨考虑一下模型和方法的偏差如何扭曲一个从一开始就关注家庭问题的研究项目的发展:关于「家庭等价规模」(household equivalence scales)的经济学文献。这种量表根据家庭规模和组成的差异调整家庭收入的衡量方法。这些衡量比例在日常政策中被使用,例如,在不同规模的家庭中设定公平的社会福利水平,以及被研究人员用于研究收入分配。 然而,有关家庭等值尺度的经济学文献已经越来越远离和政策有关的问题(Nelson, 1993年a)。首先,虽然政策的实施往往集中于儿童福利(例如,在确定援助有受抚养子女家庭的水平时),但将这种问题塞进效用理论框架(其中,等价规模被解释为支出函数的比率)的做法,导致家庭福利通常被建模为给成年人的福利。而一些最受推崇的模型暗示:当儿童存在时,成年人不会购买主要由儿童消费的产品,而是购买其替代品(substitute away)。第二,虽然等价衡量比例的早期实证评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规范性预算研究,其中列出了每种类型的家庭在食物、租金等方面的「需求」,但最近的实证实践的特点更加微妙复杂。不幸的是,使用大规模的需求系统回归来估计等价规模,在一段时期内在是一种常规做法,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被证明在根本上无法进行有效估计(因为同样的需求方程可能与任何数量的支出函数相一致)。 虽然许多经济学家遵循这些依赖选择理论和高级计量经济学的趋势,但Trudi Renwick和Barbara Bergmann(1993)最近的一篇文章说明如果当关注的焦点更接近政策问题,而不那么愚忠于特定的模型和方法时,可能可以实现什么。Renwick和Bergmann为不同组成的家庭制定的「基本需求」预算遵循早期的规范预算编制方法(prescriptive budget approach),并根据时代变化增加了育儿支出项目。虽然技术上不复杂,但人们实际上可以从这种直接的(尽管确实是近似值)证据中学到更多关于成本的知识,而不是从虽然复杂但既无焦点又不直接的技术中学到更多。  经济教学
经济教学围绕形式的理性选择模型定义的一门经济学学科,也许会附带一些事实,可以通过一种纯粹专注于传递预设知识的教学风格而被延续下来。然而,如果经济学的定义更加宽泛,这样的方法可能是不够的。培养对经济问题进行批判性、分析性和创造性思考的能力需要一种不同的教学方法。虽然这样的思维方式可能和当前的方法一样可教,但如上所述,它不一定是那么容易教的,也不一定是用同样的教学方法可以教的——甚至可能是需要教给完全不同的学生。  图源:https://www.colgate.edu
图源:https://www.colgate.edu女权主义经济学家认为,不仅是经济学课程的内容,使用的教学风格也可以经历有益的转变(Strober, 1987;伯格曼,1987;Bartlett和Feiner, 1992;沙克尔福德,1992)。一些学者则强调使用实践学习和实验室会议,让学生与模拟情景互动工作,收集自己的访谈数据,和/或分析数据,给学生更多的机会「做经济学」和解决问题(Bartlett和King, 1990)。有人认为,女性主义教学法要求教授和学生之间有一种不同的关系:教授和学生之间的距离更短,对话更多,学生之间也是如此。有些人明确建议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学习的情感方面(Strober,1987)。 当然,女权主义者并不是唯一对互动和合作学习感兴趣的教育者;对许多教育工作者来说,这只是「良好的教学法」,正如对学生实际学习方式的研究所证明的那样。然而,女权主义理论家更可能认为,对教育改革的抵制植根于性别和价值的文化联想。这些教学观点应该应用于整个课程,而不仅仅是「女性与经济」课程。主动的学习技巧可以改善即使是比较熟悉的经济分析形式的实践。可以说,使用批判性思维能力在对统计学方法的选择或显著性测试做出正确判断时,就像在写一篇关于反歧视政策的文章时一样重要。 许多女权主义者感兴趣的一点是,经济学教育可能会微妙地塑造未来经济学家的人口构成。关于「课堂氛围」—— 包括教师与男女学生的互动模式和教科书中的性别刻板印象 —— 可能会使女性在特定领域取得成功的信心降低(Hall和Sandler, 1982;费伯,1990)。在经济学的话题、模型和方法上,标准的男性中心主义偏见可能会使女性学生受到潜在影响而相信「经济学不适合(或不关于)我」。当前过于强调数学技术也会导致那些满足于抽象思维但在更广的分析思考上薄弱的男女学生进行自我挑选, 而那些拥有良好分析技能却不认为这些技能适用于经济学的学生会把自己排除在外。这样的选择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学生和教师都对现状投入了大量精力。 
总结 女权主义经济学,重申一下,不是女性经济学,不是只由女性实践,也不是只使用软技术和合作模式的女性经济学。女权主义学者认为,由于经济学在其模型、方法、主题和教学中含蓄地反映了一种扭曲的男子气概理想,经济学变得不那么有用了。女权主义学者认为,使用更全面的工具来研究和教授更广泛的经济活动领域,将使经济学成为一门对男性和女性实践者都更有成效的学科。 许多读者可能已经发现自己在某些方面已经在实践「女权主义经济学」了,虽然有些人更愿意认为自己只是在研究「好的经济学」。如果某些人非常反感把自己的工作描述为是女性主义的,那么问问自己这种不舒服的根源可能会有所启发。也许这种防御性反映了关于男性和女性,以及优越性和低劣性的文化信念。这些都是需要检验的。/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Philosophia 哲学社
推荐阅读:
版权声明:“备战深国交网”除发布相关深国交原创文章内容外,致力于分享国际生优秀学习干货文章。如涉及版权问题,敬请原作者原谅,并联系微信547840900(备战深国交)进行处理。另外,备考深国交,了解深国交及计划参与深国交项目合作均可添加QQ/微信:547840900(加好友时请标明身份否则极有可能加不上),转载请保留出处和链接!
非常欢迎品牌的推广以及战略合作,请将您的合作方案发邮件至v@scieok.cn本文链接:http://shenguojiao.scieok.cn/post/2131.html
-
<< 上一篇 下一篇 >>
女性主义经济学是什么?(下)/ 翻译
20244 人参与 2021年06月30日 09:51 分类 : 深国交哲学社 评论
search zhannei
深国交2024年英美本科录取小计
-

未标注”原创“的文章均转载自于网络上公开信息,原创不易,转载请标明出处
深国交备考 |
如何备考深国交 |
深国交考试 |
深国交培训机构 |
备战深国交 |
联系方式
Copyright www.ScieOk.cn Some Rights Reserved.网站备案号:京ICP备19023092号-1商务合作
友情链接:X-Rights.org |中国校园反性骚扰组织 | 留学百词斩 | 南非好望角芦荟胶 | 云南教师招聘考试网 | 备战韦尔斯利网| 备战Wellesley